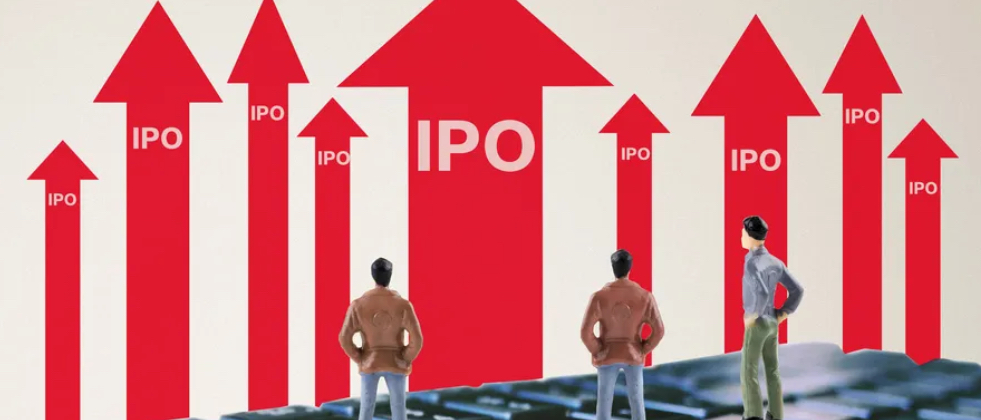
專門給農民放貸,是一門好生意?
文/每日財報 張恒
繼今年年初首次向港交所遞交IPO申請卻因遲遲未有新進展以致招股書失效后,這家專注于給農民放貸的公司---中和農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和農信”),近日再次向港交所發起沖擊。
9月27日,港交所官網披露了中和農信最新上市招股書,中金公司為其獨家保薦人。在招股書中,除此前業績數據之外,中和農信還更新了2024上半年各項經營業績數據,得以讓我們更加全面了解到該公司目前發展情況。
招股書開篇就詳細介紹了中和農信的成長背景,資料顯示,中和農信的歷史可追溯至1996年,前身專為四川省秦巴山區扶貧提供貸款而創設的小額信貸扶貧試點項目,而后在2000年,由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全面接管。2008年11月,中和農信農業集團有限公司成立,通過向小農戶和農村小微企業主提供金融及非金融產品及服務,助力中國縣域農村地區產業發展。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的報告,按截至2023年12月31日總貸款余額計算,中和農信是面向中國農村市場的最大非傳統金融機構,市場份額約為8.6%。
而在中和農信快速發展的同時,其深耕農村市場的金融服務模式和經營業績情況始終是市場關注的焦點。那么,專門給農民放貸,是一門好生意嗎?中和農信近些年自身經營質量與效益到底又如何呢?
明星資本紛紛下場增持 高管團隊經驗豐富
從慈善組織到完成向信貸公司“華麗轉身”后,憑借著在覆蓋中國廣闊下沉農村市場長尾客戶的加持下,中和農信自然吸引到了眾多明星資本的下場加盟,紅杉旗下萬事安、國際金融公司、螞蟻集團、TPG、淡馬錫、中金公司等均在多輪融資中紛紛現身,累計跟投資金約超30億。
在早期的融資過程中,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牢牢占據中和農信第一大股東的位置。不過自2017年開始,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在中和農信的多次股權交易中,陸續將手中持有的股份分別轉讓于螞蟻集團全資子公司的上海云鑫以及中金公司旗下的CWI,最終實現了退出。
在2018年9月,上海云鑫通過增資及股權轉讓等方式拿下了中和農信最大股權,躍居成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達到34.173%。此后,上海云鑫則將持有的全部股權轉至螞蟻集團另一全資子公司API名下。
直至2020年中和農信進行C輪融資,TPG入股后,中和農信股東結構再次發生重大變化,截至此次IPO前,螞蟻集團通過全資子公司API持有27.36%股權,退居為第二大股東;第一大股東則變為TPG,其聯署公司The Rise Fund和NewQuest分別持股19.71%、8.95%,合計28.66%。
此外,加拿大排名前5的OTPP(安大略教師退休基金)、淡馬錫全資持有的Impact Blossom和Impact Asia分別在上市前持有中和農信15.89%、9.46%股權。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港股上市的獨家保薦人中金公司,則通過CWI持有中和農信2.21%股權。
進一步股權穿透,我們還發現,中和農信在國內的主體公司---中和農信農業集團有限公司,旗下還直接或間接控股了諸多企業。其中,100%全資控股的附屬公司多達20家,大多數是以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小額貸款公司為主;另外有2家間接控股的公司,分別為北京鄉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85%)、北京小鯨向海保險代理有限公司(持股25%)。
再來看中和農信的高管人事方面,雖然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已不再持有中和農信股份,但公司目前僅有的兩位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劉冬文博士和首席財務官李真女士,兩者皆擁有多年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的任職經歷。
招股書顯示,現年51歲的劉冬文,擁有超過28年的農村發展項目管理經驗,在創辦中和農信之前,曾于1996年至2001年間擔任中國扶貧發展中心的項目主管,負責項目的設計、管理、監督以及評估工作。
此后,劉冬文任職于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2002年6月至2008年12月,先后擔任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的項目主管、小額信貸項目部主任、基金會副秘書長等職務。
現年52歲的李真,于2008年11月加入中和農信,至今一直擔任數家附屬公司的副總裁、總經理,以及旗下多家公司的董事及董事長要職。而在加入中和農信之前,李真曾在中國建設銀行、招商銀行,以及多家會計師事務所任職,直至2008年7月起開始擔任中國鄉村發展基金會小額信貸項目部財務總監。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中和農信第一和第二大股東的TPG、螞蟻集團,都與其有著相當緊密的人事關系。比如,作為第一大股東的TPG,其中國區主席孫強和負責大中華區醫療投資的蔡俐,目前兩者都擔任中和農信非執行董事一職,主要負責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和建議。
而螞蟻集團則是向中和農信輸送了不少高級管理人才,如擁有螞蟻集團背景的支付寶高級專家、螞蟻云創資深技術專家趙占勝,現任中和農信首席技術官兼副總裁。而螞蟻集團企業發展部資深總監朱超,早從2018年5月起就一直擔任中和農信的董事一職。
業務結構較為單一,運營成本上升掣肘盈利
分析完了中和農信股權結構和高管人事等宏觀層面,讓我們再將眼光重點聚焦在其商業模式和經營業績微觀層面上。
和許多中小型貸款公司一樣,中和農信的商業運作模式主要為融資產生資本金,然后將這部分資金以貸款形式發放出去賺取利潤。
從資金來源來看,中和農信對外發放貸款的資本金主要由表內貸款和表外貸款兩部分構成。所謂表內貸款,是指中和農信利用自有資金發放的貸款余額;表外貸款則是指通過助貸業務發放的貸款余額,以及聯合貸中由銀行等合作方出資的部分余額。
招股書數據顯示,2023年之前,表內貸款一直為中和農信在貸余額的主要生力軍,2021至2023年,公司表內貸款在貸余額分別為106.48億元、98.66億元和100.66億元,占比分別為71.1%、65.1%、52.7%,但到了2024年上半年,其表內貸款余額降至99.89億元,占總在貸余額比重降至50%以下,僅為49.4%。
相反的是,中和農信表外貸款余額和占比卻都一直在提升,已經從2021年末的43.33億元,占比28.9%,逐年增長至今年上半年末的102.16億元,不到三年時間增長了135.77%,同時占比也大幅提升至了50.6%。
由此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和農信貸款規模在不斷提升,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總在貸余額已經達到了202.05億元。那么,如此巨量的貸款,中和農信到底發放給了誰?
毫無疑問,是下沉邊緣市場中千千萬萬個小農戶,數據顯示,2021年-2023年及2024年上半年(以下簡稱“報告期”),中和農信在農村普惠信貸業務上所取得的收入分別為16.61億元、18.35億元、20.23億元和11.66億元,所占總營收的比重分別高達74.7%、75.5%、63.6%及60.7%。
除此之外,雖然中和農信還布局了農業生產服務、農村消費品及服務和農村清潔能源服務等諸多業務,但這些板塊所對總營收的貢獻度并不高,還遠不及其農村普惠信貸業務。也就是說,拉動中和農信營收增長的核心仍是放貸業務。
招股書數據還顯示,截止目前,中和農信已累計向300萬農民合計放貸760萬筆,累計放貸金額1618億,按此計算,相當于每筆人均貸款2.13萬元。可見,中和農信能夠在非傳統金融機構中,做到農村市場借貸排名第一的位置,靠的還是以量取勝。
然而,這種單一的以放貸業務結構為主的商業模式,同樣會使得中和農信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一旦市場環境發生變化或者競爭加劇,公司的業務穩定性將受到嚴重影響。此外,由于農村市場的特殊性,農戶的還款能力和意愿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也增加了公司的業務風險。
照理說,由于我國農業人口基數較大,給一眾小農戶放貸能夠讓中和農信賺得盆滿缽滿,但現實情況卻是該公司盈利情況并不穩定。
各報告期內,中和農信分別實現總營業收入22.24億元、24.29億元、31.81億元及19.2億元;盈利方面,2021年、2022年其凈利潤分別為-0.36億元、-1.99億元,2023年成功扭虧為盈,實現凈利潤2.06億元,2024上半年同樣延續了盈利態勢,實現凈利潤0.79億元,但相較于2023年同期的2.8億元的盈利卻大幅下滑了71.79%。
事實上,因為商業模式的緣故,中和農信居高不下的運營成本要比一般小貸公司高,成為掣肘自身盈利增長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廣大農村由于地處偏遠,互聯網滲透率低,這部分長尾客群成為不少互聯網金融機構難以染指的增量。而之所以中和農信能在這種背景下,還可以取得不錯的增長,主要依仗的是其特有的熟人社交模式帶來的助力。
招股書顯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和農信的業務覆蓋全國23個省份的550余個縣域,扎根超過10萬個村莊,輻射近2億農村人口。截至同日,該公司在約550個農村本地服務網點中依靠超過7200名服務團隊成員和約12.7萬人的村級合作伙伴直達農村用戶,只為給農民放貸。
如此一來,中和農信的運營成本當然只會高不會低。如下圖所示,各報告期內,其銷售成本和銷售及營銷開支總計分別為11.79億元、12.89億元、19.94億元和11.54億元,兩項成本指標的費用率分別總計高達53%、53.1%、62.7%和60.1%。
借貸利率近18%,中和農信放“高利貸”助農惠農?
不難發現,“熟人經濟”是中和農信信貸業務的獨有特點,即借款人借款時,需要身邊一位熟悉的個人為其提供擔保。可以說,中和農信扎根農村市場,深諳農民訴求,確實開辟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特色化道路,為“打通農村金融的最后100米”走出了一條路。
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中和農信放貸對象是征信相對空白的農村人群,近兩年來,該公司貸款風險也有所抬頭。招股書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末,中和農信自有資金貸款30天以上違約率達到了3.56%;自有資金貸款90天以上違約率,同樣達到了2.65%,而這兩項指標在2021年之時才分別僅為1.53%、1.13%,貸款風險加劇幅度不可謂不大。
而造成如今農戶選擇高違約情況的背后,則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客戶無法承受中和農信高利率不得已而為之。實際上,與城鎮居民所能接觸到的其他貸款渠道相比,中和農信的利率一直都較高。報告期內,農戶通過中和農信平臺獲得的貸款的實際年化利率分別為17.5%、17.9%、17.7%、17.8%及17.8%。
但根據最高法關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規定,該指標是不超一年期LPR的4倍,而2024年9月發布的1年期LPR報價則為3.45%,由此計算,當期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是13.8%,中和農信顯然是遠遠超過了該水平。
對此,中和農信在招股書中給出的說法是:經修訂的司法解釋,并不適用于持牌金融機構;持牌小額貸款公司的上限,是每年24%。
而這種較高的利率水平,似乎與中和農信一直對外宣稱的“普惠信貸”、“惠農助農”定位相違背。
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我國農村普惠信貸市場規模從2019年的5.4萬億元增長至2023年的9.2萬億元,期間復合年均增長率為14.2%。然而,根據預測,未來我國仍有預估總計10.8萬億元的信貸需求在農村地區未能及時被滿足,意味著該需求比農村普惠信貸市場目前所能提供的需求要高出1.2倍。
擁有廣闊且信貸需求敞口持續向上長尾客群的下沉市場,一直是中和農信的主戰場,但在市場空間持續擴容的當下,其還需要時刻警惕來自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等傳統金融機構,以及其他非傳統金融機構的貼身肉搏之戰。
要知道,目前我國整個農村普惠信貸市場前五大參與者均為傳統金融機構,總貸款余額分別為1.2萬億元,9000億元,7000億元,5000億元和4000億元。而作為對比,截至2023年末,中和農信的普惠信貸市場總貸款余額才僅為191億元。
身處內憂外患環境下,中和農信能否借助IPO之風順利實現上市,從而克服自身目前所存在的種種難題繼續深挖下沉市場,一切還是未知數。

